本文由《南都周刊》发表于2008年12月05日,采编记者:陈建利、夏春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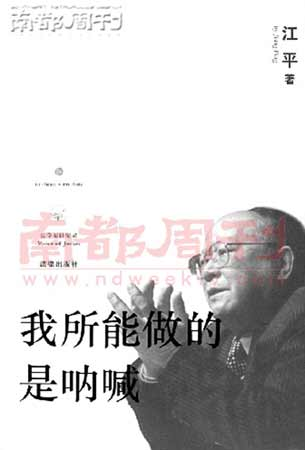

江平 著名法学家
中国要搞宪政社会主义
南都周刊:“呐喊”是你现在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吗?
江平:(笑)这本书是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近期的演讲集,他们挑了里面的一句话做标题,我也同意。这个标题有两个意思。第一,我现在已不参与任何的人大和其他方面的工作,仅是一个教授。第二,作为搞法学的,希望中国现代的法律精神能够得到更高的贯彻。现在看来离这个还有距离,希望在中国的法制建设上,现代法制理念、现代宪法精神上、民主政治上能够呐喊一下。也许有人感到我把自己抬高了一点,与鲁迅的“呐喊”类比,但现在中国的确需要在宪政理念和法治精神上呐喊。
南都周刊:“我所能做的只是呐喊”,这里面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但也有一种悲怆的感觉。
江平:过去我担任校长也好,在全国人大参加立法工作也好,我所能做的还多一点。现在只担任教授,我只能是发声呼吁。当然,第二层意思也很明确。如果现在社会很理想了,当然不需要呐喊了,就是因为现实与理想还有很大的差距。
南都周刊:你曾谦虚地说,你没有读过多少法学名著,也没有写过法学名著,你更多的是一个法学教育家和法律活动家。你们这代人既经历了“反右”和“文革”的切肤之痛,也参与了改革开放后的立法工作和宪政呼吁,你怎样看待你们这一代法律人的使命?
江平:在中国一百年以来的法学人中,刘桂明把我们看作第四代法学人。我们这一代是1930年出生的,1949年正好是十八九岁的年龄,参加了革命,也参加了新政权的建立。在那个时代,我们上一代的法学家,除了搞国际法的,后来得到了一些重用外,其他的都被看作是旧法人才。
南都周刊:您78年的人生历程,无论是受到的屈辱磨难,还是获得的荣誉褒奖,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无不交织在一起,回首时你会有什么复杂的感想?
江平:从我们这一代法律人来说就是两个。第一是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,是一个很坎坷的道路。从开始1949年比较注意法制和法律,1951年第一批派到苏联留学的300多个人当中,专门派去学法律的就是12个人。学苏联,苏联也注重法律啊。但1957年反右以后,尤其是文化大革命,越来越法律实用主义,践踏了法治,导致了十年浩劫,这三十年我学的法律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南都周刊:留下了很多遗憾。
江平:很大的遗憾,我学的东西一点也用不上,国家也不要法律。但改革开放这三十年,我们也应该看到,中国的法治建设确实和前三十年完全不一样,对法治的重视,法律人才的培养,包括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。改革开放有两个轮子,一个是市场经济,一个是法治。
但我们要看到这三十年有进有退。总的是进步了。我常常说是进两步,退一步,今天这进了,明天那又退了,也有不少遗憾。现在宪政怎么样?宪法权力保障怎么样?言论和新闻方面连法律都没有,还都是空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改革开放三十年,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快,市场经济建设快,而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,人权保障发展方面,法制完善方面还是相对滞后的。但中国终究走上了一条正确的、健康的、法治的道路,还要进一步走上宪政的道路。现在不是就到底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展开争论吗,我的发言就是搞宪政社会主义。
南都周刊:像这本演讲集所呈现的,你近几年不断地在一些公开场合,在媒体上发言呼吁,觉得有紧迫感?
江平:当然,但不能理解为,我呐喊好像我就是先知先觉。现在社会的确是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力量,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宪政的重要性。为什么说“呐喊”?就在于环境开始封锁你。
南都周刊:你在演讲中多次提及,你一生坚守的一个理念就是“只向真理低头”,很难吧?
江平:你们这代人没有经历前三十年。那时,如果一个人还能维持基本的做人标准和理念,不说假话,不说违心话,是非常难的,因为政治环境和政治压力。而这三十年来,一个知识分子能保持本色,是就是是,非就是非,也不容易,有些是环境的压力,有些是做官的诱惑,有些是利益的诱惑。
我说这句话,包括是对自己的勉励也好,对学生的勉励也好,那就是知识分子,如果是官方的知识分子,当然要为官方利益去做,但起码有个做人的道德标准。但如果是非官方的,更应该秉承这种东西,应向真理低头。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,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下,人们往往模糊是非,没有原则。
南都周刊:你在法学界一直受大家尊重,被认为是“中国法律界的精神脊梁”、“中国民商法之父”,你怎样看待这些声誉?
江平:这些说法不合适。
南都周刊:为什么?
江平:历史是由若干的历史事件构成的,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。1957年反右我敢说真话,90年代我又说“只向真理低头”。也许人们从这些历史事件中,对我形成这样一种评价。但法律本身,尤其是民商法的精神就已经铸就了这样。
并不是有法可依就叫法治,有宪法就可以说是宪政。宪政就是民主精神,法制精神,人权精神。这些精神就应该是法律人秉持的。搞民商法的,还要加上平等精神。市场经济不讲平等怎么行?我们学法律的去教导别人,教我们的学生要秉承宪政理念,我们自己更应该按这个理念去做。搞法治的人说透了,就是要问问自己,你所追求的法治理念有没有一些普世性的东西。不能一说到法治理念,就想到中国特色,一讲中国特色,普世性的东西都没有。让我欣慰的是,现在年轻的法学人中,有很多比我更强烈地坚持自己的法治理念。
南都周刊:你说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,天生如此吗?
江平:很多事很难说是天生的。我乐观主要有两个原因。一是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现代法治理念的普及相当快,学生接受这些东西也相当快。二是现在法律院校里面培养出来的人,将来会在中国的各个领域起着重要作用。学法律的走上政界,这是个世界趋势。不要说美国等西方国家,就连俄罗斯都是典型。普京、韦德梅杰夫、还有原来的戈尔巴乔夫,都是学法律的。这些人早晚会成为政界里面的人物,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南都周刊:你对中国的宪政之路也比较乐观?
江平:一个国家的最终法治建设如何,还是要看掌握法院,检查院的,做律师的,掌握国家各个政权系统的人,他们那些人的法治意识怎么样。中国现在的依法行政,与二十年前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虽然现在有很多问题,但很多观念都不一样了。现在讲“有限责任政府”,讲“政府制约”,过去谁讲政府要制约啊。
南都周刊:那中国的宪政之路可能的突破口在哪?
江平:依法行政和民主选举,这是最重要的两个。吴敬琏教授呼吁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,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须要限制政府的权力,政府的作用必须有限度,而且必须有监督和制约。第二个就是民主选举、基层选举。今年的选举法要修改,党内民主也包括在内。这两个是比较容易着手的。
当然,这里面更困难的是要确保宪法里面的公民权力,17大已经提出要保障公民的表达自由。我们表达要自由的话,就要出台新闻法、出版法等法律。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最大的问题。当然还要发展社会组织。我们老讲的环保靠什么?光靠政府能把环境搞好吗?西方要靠多少个民间的组织啊。为了防止日本人捕鲸,世界有很多民间组织在行动。但中国现在对民间组织的发展往往很害怕,社会公益事业或环保必须要有民间组织的参与。
南都周刊:你在文章中也多次提到过,在界定国家权力与公民私权之间,要还社会以权力,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?
江平:是啊。政府控制这么严,民间组织怎么发展啊。其实,中国最根本的腐败问题也只能通过宪政才能解决。不能光靠内部人监督或内部的监督机制,还要靠舆论监督和社会组织的监督等。
中国有些事情急不得
南都周刊:近年来,中央政府一直把民生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,包括医疗教育等,但现在也有一种很尖锐的批评,认为在中国当下阶段只重民生,而忽视民权,形同养猪。你怎么看这一观点?
江平:这个批评的意见有它合理的地方,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。宪法实际上是三大自由、三大权力。一是民法中的权力,包括财产权,合同订立自由等。第二个是社会权力,包括教育、医疗、保险、社会保障等。第三个是政治权力。现在民事权利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,财产权也写进宪法了,私人财产权虽然被侵犯的还很多。民生主要涉及的是社会保障的权力,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。政治上的权力。我们现在可以举出很多例子,就是说一个人被抓了,三年五年都不审理,或者判错了,像这样的问题,还应引起高度重视。温总理说了,中国要加入联合国关于人权的公约。
南都周刊:今年的大部委改革,可以说是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与尝试,你怎样看待这一改革?
江平:中国的政府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的。这不仅仅说是中国的人多。若算上党的机构、人大政协、证监会、电监会等事业单位,他们实际上也是公务员编制的,公务员跟老百姓的比例是最大的。所以减少中国的机构庞杂对解决官僚主义,解决政府效率低下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政府机构的改革涉及到权力问题,利益分配问题,所以要有心理准备,它不会改得彻底,中国历次的机构改革都陷入了精简-膨胀的怪圈,这次也很难逃出。大部制是不可缺少的,但不过是一种形式,绝不是一切。重要的还是要明确权力界限,权责对等,且要有监督机制,包括内部的监督和外部的有效监督。
南都周刊:近年来,你一直为中国的宪政鼓与呼,在这个过程中,感受最深的是什么?
江平:2004年宪法修改的时候我是挨批的。当时人大常委会召集了一个会议,有八个法学家参与,我也参加了,后来在网上讨论了,结果说我们是私人修宪。宪法修改不许老百姓知道,不许见报,不许法学家讨论,这是一个天大的荒谬。我想这件事也说明中国的宪政之路还很长。这样的例子很多,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